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说到文字狱,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清朝。诚然,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为了控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非常重视在思想领域进行高压管控,清朝历代皇帝都把控制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为了堵住“反清复明”的任何可能性,清政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清朝并非中国古代王朝中唯一一个兴起文字狱的朝代,不夸张的说,所有封建专制王朝,都能“熟练”的运用文字狱来维持稳定。如果从牵涉的人数、惩罚的惨烈程度等纬度来衡量,汉人朱元璋一手缔造的明朝,才是大一统王朝中文字狱的最高潮。
为什么说明朝的文字狱最惨烈呢?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清朝时期的文字狱,然后再与明朝时期进行比较,就能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
事实上,满人刚刚入关时,比如从多尔衮到顺治时期,满人主要是依靠军事手段打服汉人的抵抗情绪。在清朝逐渐稳定之后,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所谓的康乾盛世中,文字狱尤为激烈。
在清圣祖康熙时期,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文字狱。
一次是康熙幼冲时期的朱国祯遗书案,湖州富户庄允诚刊印朱国祯的《明书大事记》、《大政记》、《大训记》及未完成的《明书》一部,这些书中直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讳,且奉和清作战的南明为正统。
此时清朝的实际掌权者是飞扬跋扈的鳌拜,为了立威,他从重从严的处理了此案,将庄允诚满门抄斩,妻女发配黑龙江为奴。整个案件中,共有220人被处决,堪称清朝杀人最多的一次文字狱。
第二次是康熙亲自执政后发生的戴名世案。和朱国祯的遗作一样,戴名世也在自己的著作《南山集》中尊奉南明为正统,甚至直斥顺治为“僭越”。在刑部审判后,建议康熙诛杀300余人。但康熙慎之又慎,最后仅将戴名世处斩(刑部原拟凌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在雍正一朝,文字狱更多和高层的政治斗争有关,比如雍正在打倒年羹尧时,鸡蛋里挑骨头,找一些无关紧要的错别字来寻晦气,还因此牵连出了曾入年羹尧幕府的汪景祺案。
无独有偶,为了打倒隆科多,雍正刻意指责查嗣庭“维民所止”的“维止”是“砧”了“雍正”二字的“头”。通过把查嗣庭打为隆党,雍正借机清除隆科多多年来在政府中的影响,这次文字狱的本质仍是高层权斗。
对于湖南曾静一案,雍正亲笔写下了《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但却放过了首犯曾静及其徒弟张熙,让他们作为“反面教材”“警醒”世人。
清朝的文字狱在乾隆时期达到高潮,但乾隆更多是通过思想的高压管控来达到目的。比如通过编撰《四库全书》,清廷从民间搜集了大量不符合“正道”的“野史”和“妖书”,并将其付之一炬。这才是乾隆“文字狱”最“精髓”的部分。
可以看到,清代尽管文字狱迭兴,但除了第一次鳌拜大开杀戒之外,大多数的清朝文字狱并没有株连过多,除了“核心”案犯,其他从犯也少有被杀头的。相比之下,明朝的文字狱,则要残酷血腥的多。
明朝,不仅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古代专制王朝,同时也是专制皇权走上巅峰的朝代,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独夫权力,为了自己一姓江山社稷永固,明朝的皇帝们积极寻求通过限制思想,控制舆论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
在朱元璋朱棣最初两位皇帝的率先“垂范”之下,明朝文字狱的力度之强,牵涉之广,范围之大、特别是其血腥和残暴程度,堪称冠居中国历代之首,相比满清的文字狱,也要惨无人道得多。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是皇觉寺一小僧,这样的人,一旦获取了最高权力,不仅权力欲极强,而且往往会将内心极度的自卑,转化为血腥的杀戮甚至残暴的屠杀。
和其他朝代一样,明朝的文字狱也常常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要说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文字狱,就不得不先提洪武年间的几桩有关功臣的大案。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洪武13年,即公元1380年,隐忍已久的朱元璋突然发难,以“谋反”、“通倭”、“通虏”、“结党”等重大罪名,将位高权重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抄家灭族。朱元璋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倒胡惟庸只是他政坛大清洗的第一步,紧接着,“勋臣第一”,已经年届76岁高龄的李善长、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徐节、著名学者宋濂等人皆被以各种名义株连处决。随同这些高官勋贵一起赴死的,自然还有他们的血亲家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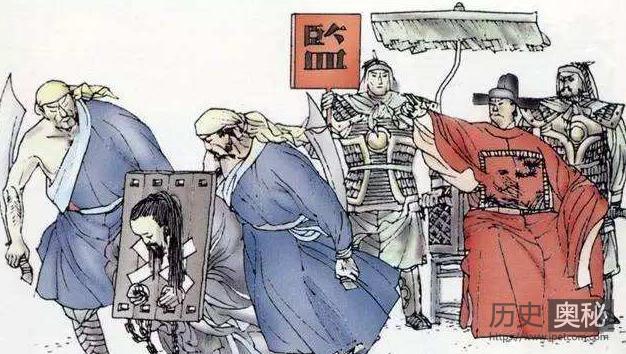 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胡惟庸一案,前后有5万余人被杀。
这把肃清之火很快烧到了军中。功高震主又作威作福的大将军蓝玉首当其冲,于洪武26年被以“谋反”的罪名族灭。之后,吏部尚书詹徽、开国公常升、东莞伯何荣、晋定侯陈桓等为明朝建立出生入死的宿将相继均被牵连杀害,他们的家属也都惨遭屠戮。
牵连蓝案而坐死的,人数也不低于4万。
加上之前徐达李文忠等人被暗中毒死,朱元璋彻底清除了可能对其子孙造成威胁的佐命之臣,《明史》感叹,“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在政治清洗的同时,朱元璋也对善于舞文弄墨的儒士高度警惕,在他看来,文人性格轻佻,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讥讽”,朱元璋时刻警醒,以免挨了骂还以为被赞美了。他总是带着最严苛的猜疑眼光,想从文人的文字后面找到诽谤皇权的把柄。因此,朱元璋文字狱的“精髓”,主要在于以下八个字:
捕风捉影,望文生义。
通过这一指导方针,朱元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无中生有的文字冤案,也由于出身低贱,朱元璋极度自卑,总是担心文人在言辞中对自己“肆行诽谤,欺君罔上”。在他的“法眼”中,也真的发现了很多“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也从中“发现”了不少“逆谋”,大批文人因此惨遭灭门和处决之祸。
比如,曾任杭州府教授的江南大儒徐一蘷循例上贺表,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谀颂之词,但在朱元璋看来,却是十恶不赦的诽谤恶言,朱元璋如此批示:
生者,僧也,以我当为僧人也;光,财发也;则字音近贼也。
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辞,其结果自然是“遂斩之”。
现在也有人指出,徐一蘷死在朱元璋之后,所以并非朱元璋所杀,但此说经不起推敲。
据现代考证,徐一蘷确切的死亡年份应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年78岁,而并非不少翻案者所以为的朱元璋死后的1400年。
在上此表笺前,油尽灯枯徐一蘷已然行将就木,这份“贺表”其实是为了此前因文字狱入狱的苏伯衡、童冀、来复向朱元璋求情,临近生命的终点,徐一蘷终于可以不管不顾的拼死一搏。
朱元璋自然不可能大发慈悲,最后的结果是,仗义执言的徐一蘷也和自己的老友苏伯衡一起,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成了朱元璋文字狱的刀下冤鬼。
也有人说,朱元璋自己也多次自陈:“朕本淮西布衣”,曾“空门礼佛,出入僧房”,以此证明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苦卑微出身并不忌讳,以此替朱元璋洗脱许多文字狱滥杀的恶名。
但自己说,和别人说,对朱元璋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自承卑微出身,朱元璋的用意其实是为了炫耀自己超过常人的非凡能力:有谁能在一无所有中,赤手空拳的打下一个大帝国?除了我朱元璋,还有谁能创下这样的伟业?正因朱元璋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才是“天命”注定的统治者。
如果其卑微的过往,被其他人提及,在朱元璋看来,那就只能是奸险之徒的贬低和讽刺了。
如果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朱元璋无疑有着非常明显的心理疾病。在大权在握之后,朱元璋变得极为狭隘,甚至可以称之为精神失常。
 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朱元璋早年没有受过教育,在兵荒马乱的饥饿交加中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刀剑和实力是唯一能保住存活下去的手段,要想活下去,就一定要比别人更无耻、更凶狠、更狡猾。也许就是在这一阶段,养成了朱元璋冷血无情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成为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独夫之后,朱元璋早年埋下的嗜血因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余地,人世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他随心所欲的肆意杀戮,这也成了他展示权力的手段:一般而言,权力欲熏心的人物非常热衷于炫耀手中的权力,权力的春药能带来的最大快感,无非是随心所欲的延续或剥夺他人的生命。
当然,也不能忽略朱元璋行为背后的帝王权术。对中国古代专制帝王而言,驾驭臣下有一条不可替代的准则:恩威不测。也就是说,始终让臣下和奴仆猜测不透自己的意图,如此,这些人就会终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也会对皇帝更加惧怕和臣服。所谓“天威难测,雨露雷霆,均是天恩”。朱元璋作为一代雄猜之主,无疑是玩弄此类权术的个中高手。
朱元璋的文字狱,不仅瞄准了同时代的高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甚至连儒家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孟子都没有放过。
在读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句时,朱元璋勃然大怒,严加斥责:这不是臣子该说的话!
朱元璋随即就命人将孟子的牌位扔出孔庙。之后,由于刑部尚书钱唐的死谏,朱元璋知道无法抹杀全天下士子对孟子的情感,就退而求其次,表面上恢复了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实际上却通过大肆删文把孟子的学说彻底阉割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和《离娄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天与贤则与贤”一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凡八十五条,都因不合“名教”而被全部删掉,朱元璋还特别下令: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取代孟子地位的,是南宋以后被奉为理学圭臬的朱熹学说,朱元璋提出,“为学自当本乎程朱”。朱熹的理学将君臣的伦理纲常上升到了天地至理的地位,对巩固皇权自是大大有利。
汉魏时期,三公尚且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随着皇权的逐步集中,特别是像朱元璋这样的文字狱打击之下,臣僚的地位一降再降,已经从最初的“圣人门徒,天子诤友”,一降再降,沦为了皇帝的仆人和奴才,有明一代,当庭杖杀朝廷命官的事例数不胜数,皇权也遥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任意践踏着帝国中的一切。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诸子之中,最像他的无疑是第四子朱棣了。在运筹帷幄,雄才武略上,朱棣确实略不如乃父。但说到阴险刻薄、残忍无道,朱棣则更可以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由于是靠造反上位,朱棣在言论管控上的需求比“天生圣人”朱元璋更迫切。他亟需消灭任何关于其得位不正的质疑,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是靠手中血腥的屠刀了。
攻破南京城之后,朱棣做的第一件事,是装模作样的参谒太祖朱元璋的宗庙,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但转过身去,朱熹就动手改写乃父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此书详实记录了朱元璋身前的言行,其中多着力培育皇太孙,明确指定朱允炆为自己的接班人的内容,也不乏训斥诸王要他们忠心事上,不得忤逆之处,这对于正在寻求“正统”的朱棣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于是,朱棣掌权后,立即开始了对史官的血腥屠杀,随后就安排自己人接手史书的修撰工作,务必充分展现朱棣“继皇考神功圣德,贻范万世”的光辉形象。
 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明朝文字狱才是历代文字狱的“巅峰”
对于那些追随朱允炆,质疑自己权威的文臣,朱棣的屠刀绝不会止于史官,在朱棣的直接授意下,替建文帝朱允炆策划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在受到非人的残酷折磨后被肢解而亡,不仅其男性家人被全部处决,女性家眷则被全数送入教坊司,纵容军校肆意轮奸;和他们有婚约的家族也惨遭流放,和灭门无异。
朱棣残暴的一面,在著名的方孝孺一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一开始,朱棣装模作样想要“策反”方孝孺,但无论软硬兼施,都对刻板遵守儒家教条的方孝孺无效。据传,方孝孺曾如此顶撞朱棣诛九族的威胁:“便诛十族,又奈何!”方孝孺也许成就了自己忠节的名声,但却害苦了也许还不想死的亲朋好友。在方孝孺一案中,前后被杀有案可查的就多达847人,其中也确有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诛十族可算是“实至名归”了。
不仅如此,负责押解方孝孺的大理寺官员刘瑞王高,仅仅因为让方孝孺在树荫下休息片刻,就被朱棣下令穿鼻处决。
朱棣杀人,不完全为了争夺权力,也是为了满足自身变态的心理。在处死了副都御使茅大方之后,朱棣还将其年过五旬的遗孀送入官娼为妓。不久,该妇就不胜摧残而病逝,朱棣闻讯后,竟然下了一道这样的圣旨:
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礼部尚书陈迪被捕后一声不吭,朱棣甚至命人将其儿子的鼻子舌头炒熟后硬塞入口中。御史大夫景清欲为建文帝报仇刺杀朱棣,不慎被发现后,朱棣下令将其本籍所在的亲朋乡邻全部诛杀,美其名曰“瓜蔓抄”,即像瓜藤蔓延一样株连无辜之人。
其报复心之重,手段之残忍,已不可以常理和人性度之,可称之为手握权力之后的兽性大发。
在对朝廷显贵大开杀戒的同时,朱棣并没有放松对民间言论和文化艺术的高压管控。
为了彻底巩固皇位,朱棣鼓励民间互相告发,任何持有建文帝时期的书籍,或者书中提到建文时期的人或事,或者某人曾经观看过类似的书籍,都在可以告发之列。一时间民间个个惶恐,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肃杀气氛。
明朝政府原本已经对民间文化做了硬性规定:
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欢乐太平不禁的,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架头杂剧...敢有收藏传诵印卖,拿送法司究治。
朱棣还嫌这样的惩罚太轻,下旨要求: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按照此令,凡家中有不符合“名教”和“律所该载”的词曲,就要杀了全家,至于什么才是律所该载,什么才算亵渎帝王圣贤,都没有确切的标准,全凭当权者的喜好来定,一如他们随意操弄小民生死一般。如此,民间仅有的一点文化残余,也被打压殆尽。
对于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朱棣也予以严厉打击。任何谈论靖难之役的,都被视为“诽谤长短,议论朝政”,对此的惩罚仍旧是惨无人道的“全家处死”。
在明王朝的高压政策下,缉拿“妖书妖言”是顺理成章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往往会演化中血腥的寻租游戏。以负责缉拿的锦衣卫而言,凡是抓获“妖人”,缴获“妖书”,就可得到重赏。于是,这些恶棍屡屡炮制出一起又一起莫须有的冤案,用严刑拷打获取“口供”,被诬陷的人中不乏朝廷命官。
有明一代,类似行为造成的冤案数不胜数,“死者填狱,生者冤号”,黑白颠倒,日月无光,活脱脱一副人间地狱的惨相。
客观地说,比起异常残暴的朱元璋和朱棣,后世明朝诸帝的行为有所收敛,但也一样充斥着血腥的冤案。
明清两朝,并称为中国专制王朝中皇权集中最甚的朝代,这样的“进步”之所以发生在明朝,一方面是因为皇权不断集中的惯性所致,一方面也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兴起的文字狱,并随之而来的肆意杀害士大夫有关,皇权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能够对其稍加制衡的士大夫的“尊严”和“节操”,则像抹布一样被踩在脚下。越是如此,皇权对言论的管控也越顺手,越严厉;文字狱越是“兴盛”,更是反过来加强了皇权的专制。古代中国专制王朝统治下臣民的苦难,就一直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加深加重,永无出头之日。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转载或引用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部分源自互联网,无法核实真实出处,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