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价司马迁:“身残处秽”,以文章“不朽”
毛主席从学生时代起就研读《史记》,对《史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对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毛主席一生中更是多次谈及,赞赏有加。
1915年9月6日,毛主席在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举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青年毛主席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在《讲堂录》里,记道:“马迁,龙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对于司马迁的生平事迹,毛主席非常熟悉。对于司马迁悲惨的人生遭际,毛主席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1949年12月,毛主席前往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在列车上,毛主席问俄文翻译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主席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主席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四十里”。
师哲告诉毛主席,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县北。毛主席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
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主席颇有些伤感,他半晌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七岁立为皇太子,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里,毛主席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师哲说:“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毛主席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
说着,毛主席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又回身望望师哲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师哲说:“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毛主席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地在烟灰缸上弹掉烟灰,说:“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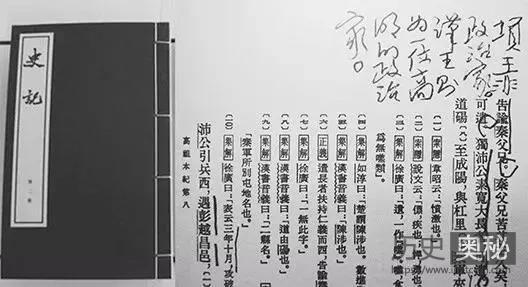 毛主席评价司马迁:“身残处秽”,以文章“不朽”
毛主席评价司马迁:“身残处秽”,以文章“不朽”
司马迁“文章”的价值,备受历代推崇。汉魏六朝时期,学者们一致推崇司马迁的“良史之才”。班彪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代的刘知几是历史上第一个广泛评论《史记》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记》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唐代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司马迁《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未有的认识和开发。韩愈爱好司马迁的文章,如柳宗元所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司马迁的文章风格,在《报袁君秀才书》中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宋代郑樵对《史记》甚为推崇,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明代方孝孺说:“《史记》之文,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澄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用“衍而虚”、“畅而杂”、“雄而肆”、“宏而壮”、“核而详”、“婉而多风”、“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等概括史马迁文章的多种风格。清人对司马迁的文章也极为推崇,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多处涉及对《史记》的评论,且有创新意义,是清代评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如他认为“《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近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地清理总结,其气魄之宏伟,识力之超人,态度之严谨,罕有其匹。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顾颉刚则称《史记》“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司马迁“文章”的不朽。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谈到: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毛主席在讲话中所引用的司马迁的“这几句话”,出自千古奇文《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所以这封书信有的选本上题之曰《报任少卿书》。任安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正当司马迁着手全面修改、审订《史记》时,又碰上了内宫巫蛊事件。这年汉武帝在甘泉有病,江充说是因巫蛊所致,并指使人言宫中有蛊气。武帝命江充入宫追查,江充报告说在太子刘据宫中掘到诅咒皇上的木偶最多。刘据迫于无奈发卫卒自卫,命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发兵,任安佯从太子命,实际上按兵不动。后太子兵败自杀,任安因“坐观成败有二心”,被武帝判为腰斩。同司马迁受腐刑一样,这又是武帝亲手制造的一起冤案。任安久仰司马迁冒死替李陵说话的精神,所以在狱中给司马迁写信,恳求搭救。此时的司马迁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史记》著述的伟业,他婉言辞却了友人殷切的恳求,回复了一篇《报任安书》。在这封书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于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作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史记》的著述。
综观司马迁一生,紧紧与《史记》相联系,他为《史记》而生,而活,而死,当他悄悄离开人间,留下的却是璨若明星的一部巨著,那里有他全部的智慧、卓识、希望、幽愤……字字都凝着他的血泪。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赞颂屈原说:“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司马迁高尚的人格,《史记》丰富的智慧蕴藏,历久弥新,熠熠光辉,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毛主席在1944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里所引,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前文所引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报任安书》做了颇具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主席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的问题。毛主席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他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
1975年,病中的毛主席与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此语同《报任安书》里所列举的遭受磨难的历史人物,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有所创造,其思路是一致的。受腐刑,对于司马迁的肉体是一种莫大的摧残,对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一种莫大的污辱;但对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对于他观察历史的深刻锐敏,对于他思想的升华,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催发,极大的提高。《史记》之所有具有深刻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千载以来感人至深,都与司马迁这一千古奇耻大辱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正如毛主席所言,“未尝不是好事”。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转载或引用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部分源自互联网,无法核实真实出处,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