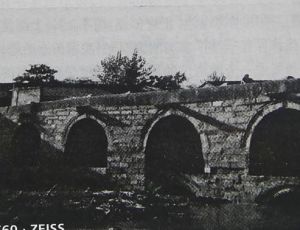谁最早将西安事变电告中共中央
由于该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又使用了言简意赅的文言文,单是“兵谏”两字,不仅高度浓缩了即将发生事变之内容,也更策略地界定了事变的性质,而且还使得“电报不长”。因此可以认为,拟定电报之人不仅在中共中央有很高的地位……
文章摘自:党史纵横,作者:孙果达。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份电报是通知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的,但这份电报究竟是谁发的却是个谜。多年来,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把张学良或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但事实并非如此。
西安事变当天的6份电报
目前可以看到的相关电报档案有6份:
第一份是刘鼎的。“当天零时,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张学良才告诉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要他即刻电告陕北的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这份电报未见档案原文,有可能来自西安事变时杨虎城的亲信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的回忆:“张随即请刘鼎立即电告陕北,说我已发动捉蒋,正在行动,请予支持。刘鼎12月12日零时30分发出电报。这是中共中央和红军最早得知西安事变发动的唯一的一份电报。”申伯纯虽然提到了电报的时间和内容,但其本人毕竟不在现场,更不是发报人,因此所回忆的其实并不算第一手史料。
第二份也是刘鼎的。“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这份电报见于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但也未见原件,而且很可能连内容也不完整。
第三份电报是张学良的。“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弟,毅(张学良的化名)。文寅。”这份电报据张魁堂在“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文称,是“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即这一电报其实也是刘鼎所发。
第四份是是东北军67军军长、秘密党员王以哲的。据高存信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二期载文称:除了文寅电,“在中央档案馆中还有王以哲于12日6时致革委电,两电内容都是告知蒋介石、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名高级将领被扣。”这就是说,张学良当天同时让刘鼎与王以哲分别向保安发出了电报。
王以哲作为张学良的主要心腹、西安事变的核心成员之一人们都比较了解,但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却不多。这一秘密的公开,起自王以哲女儿对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询问:王以哲是不是党员?罗青长请示叶帅,得到了叶帅的肯定回答,并作了正式记录,肯定了王以哲的党籍。王以哲入党的时间在1936年5、6月间,“经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王以哲的电报开头也以“同志”相称。1936年10月26日19时,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至今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数百份王以哲与保安双方的往来电报。顺便说一下,高福源也是秘密党员,由李克农介绍入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第五份电报是刘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2日中午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文明确说:“刘鼎十二日十二时电称: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获,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负伤,马志超在逃,西安及城郊之宪兵警察,及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械,蒋之卫士死二十多人,西安城郊有小小冲突,□□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我们之十大纲领等语。”这份电报未见完整的原件,特别是其中两个空缺的关键主语,不知是“我们”、“计划”还是“张杨”,但基本内容和意思已经可见,毕竟电报认为张学良宣布的是“我们之十大纲领”。
第六份也是王以哲的。“毛、周、彭同志: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弟,王以哲。文未’”这份电报的发报时间是“文未”,也就是当天的13时。看来,中共中央在上午收到刘鼎与王以哲的电报,立刻就分别复电要求确认蒋介石究竟有没有就擒。因此,王以哲的这份13时的电报与上述刘鼎12时的电报都是对中共中央询问的回答。
刘鼎的回忆
上述发往保安的电报虽有多份,但其实是两人所为。王以哲早已牺牲,所能回忆的只有刘鼎。
刘鼎是西安事变中保安方面几个主要参与者唯一留下比较完整回忆录的人。因此,在没有具体历史档案可以查证的情况下,他的回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上述几份电报的时间顺序看,刘鼎的电报应该是最早发往保安中共中央的。但奇怪的是,刘鼎的回忆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张魁堂根据刘鼎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是刘鼎的谈话《谈西安事变》。
在笔记中,刘鼎说张学良告诉他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住所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的报,“凌晨2点多,彭绍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刘鼎的笔记有五个要点:一是获得消息的时间已过12点,也就是事变发生前夕;二是发报地点是在张学良的指挥部,用的是张学良的电台;三是发报人是刘鼎的报务员彭绍坤;四是表明张学良与保安的联系起始凌晨2点多,因为此时双方电台接通;五是一个“又”字表明张学良在发文寅电前,确实已经让刘鼎向保安发过决定发动事变的电报。
概括以上五点,就能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刘鼎从事变一开始就在张学良的指挥部,参与了整个事变过程;二是从“凌晨2点多”起,张学良的指挥部就保持了与保安的联系;三是最早告知保安的电报内容,是关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开始而不是结果。
在谈话中,刘鼎肯定地说:12月12日0时,张学良告诉我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都不敢耽搁,赶快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刘鼎的谈话有三个要点:一是张学良在行动开始时就通知了刘鼎;二是全城断电无法发报,强调“步行”去远处购买电池;三是事变结束后才发出电报。
 谁最早将西安事变电告中共中央
谁最早将西安事变电告中共中央
概括以上三点,也能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刘鼎表明自己在事变过程中不在现场;二是表明与保安的联系起始于事变结束后。
对于刘鼎截然不同的两种回忆,有论者在《近代史研究》的《西安事变发动时间考略》一文中认为:“此两说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确实,且不谈刘鼎在有自备发电机的张公馆内的电台根本就不可能受断电的影响,即使作为保安常驻西安的联络员,岂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地脱离岗位。但是,刘鼎的笔记是私人性质的追记,并没有想到身后会被发表。刘鼎的谈话却是准备公开发表的,不得不顾虑当时依然还健在的张学良的安全和声誉。两相比较,笔记的真实性显然远大于谈话。此外,尽管刘鼎的两篇回忆内容大相径庭,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根本没有表示过他向保安所发的电报是西安事变时的“最早”。
对于刘鼎,他最初身份是中共中央常驻东北军的代表,后来变成了联络员,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认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在张学良身边原有的重要地位,变化起自共产国际的怀疑:“这是因为王明等人此前已两度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对刘鼎出狱及被捕后的表现提出怀疑,坚持不应让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中共中央虽然通过与刘鼎的交谈,特别是对刘鼎在张学良处工作的长时间考察,并不相信王明所说的情况,但终究不能不多少有所顾虑。”于是,受到了怀疑的刘鼎同时也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甚至在事变即将发生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这几天里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地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直到“11日中午,刘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照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说法,是有些‘恐怖’的味道。”另据《党的文献》所发表的《对<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文的研讨》中指出,了解刘鼎情况、刘鼎在北京住所的邻居、当年共同参与西安事变的孙达生说:“刘鼎生前思想上已起了变化。刘鼎后来了解到王以哲跟中央紧密联系,彼此往来电报数百份后,说当时我不了解这些情况。”
还应该指出,当时李克农交给刘鼎的两套密码,可能并不是用来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而是需要通过军委二局曾希圣的电台中转的。《党的文献》曾经载文,指出刘鼎的电台必须“经曾希圣台中转”。《曾希圣传》也指出:“12日8时,军委二局侦收到一份密电,值班人员没能全译出来,曾希圣接过这份缺字很多,连不成句的电文,发现是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当即用电话报告毛主席。”这份必须由曾希圣亲译的残缺电报,很可能就是刘鼎用涂作潮装配的5瓦小电台发出的。因为功率太小,又是在市内干扰严重的情况下发报,电文有所脱漏就非常可能。
由此看来,刘鼎其实不是西安事变的核心知情者,许多秘密他完全不了解,似乎也不够能与毛泽东直接联络的级别,因此不可能成为事变后最早向中共中央报告的人。
按照常识,要确定发报时间先后的过硬证据,其实并不取决于发报人,而应该是收报人。既然目前无法界定究竟谁是最早的发报人,那么在保安有没有最早的收报人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机要科科长叶子龙。
叶子龙的回忆
对于毛泽东收到关于西安发生“兵谏”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当年的机要员童小鹏在“目睹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回忆文章中证实了叶子龙的回忆:“译电员朱志良急匆匆地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我和叶睡在一个小炕上,也都醒了过来。叶子龙不懂得‘兵谏’是什么意思。他以为我文化高一点,能懂。可我也不懂。”
关于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得到的第一份电报只有3个人亲眼见过,除了译电员和毛泽东,就只有叶子龙。叶是当年的机要科长,又是亲手把来自西安的第一份电报交给毛泽东的,其回忆的唯一性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因为他才是首份电报内容真正的目击者。他的回忆有4个要点:一是电报到达的时间是凌晨;二是电报的收件人是毛泽东;三是电报的整体内容他“看不大懂”,因此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四是电报内容中有“兵谏”两字,使他颇费思量。
看了叶子龙的回忆,起码会有4个结论:一是电报到达的时间应该是在12日的零点前后,否则毛泽东决不会有“明天”的概念;二是电报内容一定是报告张学良开始“兵谏”而不是“兵谏”已经成功,否则毛泽东决不会让叶子龙继续睡,更不会说“明天有好消息”;三是叶子龙根本不知道西安开始捉蒋介石,否则决不会对如此大事没有印象;四是叶子龙的回忆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实际上否认了刘鼎“发动捉蒋”的电报和张学良已经完成“兵谏”的文寅电,就是中共中央收到的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也就是说,叶子龙得到的第一份电报并不是上述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份电报。那么,会不会是杨虎城发的?
据在西安事变前后一直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事先,是不是通知共产党呢?这件事往返商量了好几次。第一次决定当晚(即1936年12月11日晚上)通知,准备请毛主席派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以他们自己的通讯密码发报通知。决定这件事已到了下午六时左右。杨(即杨虎城)怕无线电报被南京方面窃收偷译出来,使机密泄露。叫人问十七路军总部李致远(原文注:专门窃收各方密报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无线电报南京方面译得出来否?李说:南京方面偷收红军的无线电是能办到的,我当年在阎锡山那里,收到红军电报很多,但能翻出的很少,南京方面我不敢绝对保险译不出来。这时,电文已拟就,为了极端机密起见,准备请张文彬以他的名字或他的化名拍发。电报是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经过第二次和张(即张学良)商量,觉得等电报到了中共那里,我们把蒋介石已扣起来了,事先不必冒此风险。至于设想的中共准备工作,迟早也不在这几个钟头。这样,电报决定不发,当即在张、杨面前,把电稿烧了。”
看来电报也不是杨虎城发的。那么,叶子龙所回忆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第一份电报的文风
叶子龙的回忆明确说电文是“半文半白”,还有“兵谏”两字。叶子龙可以说阅电无数,看不懂的必定凤毛麟角,自然印象深刻。几十年后回忆的电报内容虽然可能不太准确,但决不可能把完全可以看懂的电报错记成“看不太懂”。
张学良的电报是不是惯用“半文半白”?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就说“兵谏“二字,在事变前几乎所有的资料中,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使用“挟天子以令诸侯”、“先礼后兵”、“软硬兼施”、“硬干”、“捉蒋”等等词汇,从未出现过“兵谏”的概念。即使让刘鼎代发的文寅电中也不是“半文半白”,也依然没有“兵谏”的概念,而是用了“扣留”的字样。
既然张学良不是,那么刘鼎或王以哲是不是?回答更是否定的。刘鼎与王以哲的电报与保安保持经常性来往,不可能让电文“半文半白”,使得叶子龙“看不太懂”。
此外,刘鼎在事变过程中一直不离张学良的左右,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电台,转而用张学良的电台,让自己的报务员代其直接发报给毛泽东。拥有进入张学良指挥部这样的资格,并作出独立的决定,直接使用张学良的电台,刘鼎的级别似乎太低了。反之,张学良让刘鼎与自己并肩坐镇指挥部,并直接掌握性命攸关的电台,似乎也完全不合情理。因此,当时的刘鼎之所以能够进入指挥部,必定是他的身份最为恰当,不易使人生疑,可以充分发挥联络员的作用,才合乎事情的逻辑,也合乎张学良的身份和当时张学良已经离不开红军协助的事实。
由于该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又使用了言简意赅的文言文,单是“兵谏”两字,不仅高度浓缩了即将发生事变之内容,也更策略地界定了事变的性质,而且还使得“电报不长”。因此可以认为,拟定电报之人不仅在中共中央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越过周恩来直接致电毛泽东,而且还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又了解毛泽东与叶子龙的古文能力。电文之所以“半文半白”,可能主要就是为了电文难以破译,又让具体经手人不明其意,而唯独毛泽东一清二楚,从而达到最佳的保密程度。当然,叶子龙所言的“半文半白”,也可能是事先约定的典故或“鸽子飞了”一类的暗语。比如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命何长工和潘汉年前往敌营谈判时约定暗语:如果接到“鸽子飞了”的电报,就是红军开始出发了。结果谈判中途,何、潘收到这一4字电报,立即返回追赶部队。这类暗语的使用就使得叶子龙虽然印象深刻,却除了“兵谏”两字再说不出具体内容。确实,发出的电报要让叶子龙“看不太懂”,非高手不成。比如10月29日,叶剑英就把重要情报用文言文的电文报告毛泽东:“有主驻蒋说”,意思就是有人想捉蒋。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界定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纯系叶剑英转引张学良的意思,并非原话,因为事实证明,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时,无论在电报还是讲话中,丝毫没有“兵谏”这一极其高水准的政治概念,更何况张学良在事变前后给中共中央的众多电报中,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捉蒋行动是什么“兵谏”。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特工王戴笠》一书中说: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
综上所述,虽然还无法确认最早向保安电告西安事变的发报人,但可以肯定这人决不是刘鼎、王以哲或者张学良。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转载或引用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部分源自互联网,无法核实真实出处,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