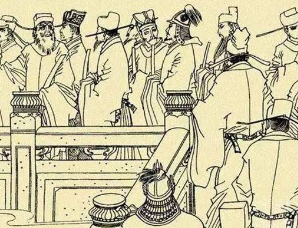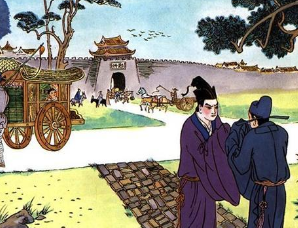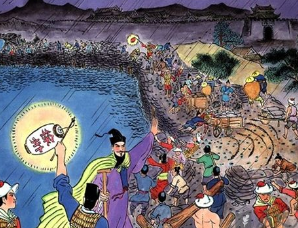王安石变法得罪了谁?
按:古往今来,没有哪个社会不需要改革,没有哪个人不希望改革。但真要卷入改革的漩涡中,原本支持改革的人,或许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派;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再义正言辞的改革,也会遭到诸多阻力。譬如说北宋的王安石,刚开始主政的时候可谓众望所归,朝野上下都希望他这名改革先锋能带来新气象。没成想,改着改着,批评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王安石变法得罪了谁?
王安石变法得罪了谁?
王安石对大宋的一片忠心日月可鉴,但没个鬼用,照样横遭政敌的恶意诽谤,被斥之为“大奸”。
要是一帮宵小之辈来指责他也就罢了,就连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特别是苏辙、苏轼兄弟这些当世大儒都来批评王安石的变法。批评变法的都是坏人吗?说欧阳修、韩琦、司马光、苏辙、苏轼这些震古烁今的知识分子是坏人?是顽固派?谁信。
推荐王家范教授的一段文字,探讨王安石变法到底为何越来越不得人心。
后代许多政治家、史论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作过多种探索,其中一种看法认为:“新法之行,荆公(王安石)固失之骤(过急)。”
这种分析对不对呢?应该说,基本上是一种皮相之见。
新法的成败关键,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说得精辟,它在于“善治者,酌之于未变之前,不极其数;持之于必变之日,不毁其度”,也就是说,能不能符合客观实际。
北宋一百多年来积累的社会问题是够多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固然使一切有识之士为之心急如焚,但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更改。这一点,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头脑是清醒的。
他在突出改革的紧迫感时,疾呼“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意在唤醒那些还在沉睡中的同僚,以为抱火厝薪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但当具体磋商实施方案时,他便显得比较稳重,预见到变法的前途充满荆棘。为此,他特别强调“(新法)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主观上还是竭力希望避免因“过急”而导致新法的受挫。
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例如“免役法”(或称“雇役法”)推行就非常慎重。
据史载,“免役法”从讨论、制订至推行,历时将近三年,开始在开封府地区试行就达十个月之久。免役法正式颁布后,许多地区大抵到第二年才逐步推开,有的则还要晚些。而且法令本身只是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各地可以参酌当地具体情况加以适当的变更。
因此,免役法虽同样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抨击,由于谨慎从事,到底是扎下了根,最后还是没有被保守派拔掉。应该指出,缓急固然与新法的实施顺当与否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新法的成败根本上要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设想是否符合实际。在这里,经济的客观法则是至高无上的。
王安石新法中遭到激烈反对、但不可逆转的要算是“免役法”。
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北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宁愿出钱雇役,而不能忍受差役的折腾,因而,改差役为雇役是中国传统王朝政权前后期一系列历史性转折中的必要的一环,是顺着经济发展的方向的。人们对“免役法”经过一个极短时间的不习惯,也就较快地适应了。
“青苗法”同“免役法”就很不一样。按“青苗法”的本意是“济贫乏,抑兼并”,含有扶助小农的意义。但是深究起来,问题就很多。
一 治标不治本
王安石的一个老朋友刘邠写信指责王安石行“青苗法”,说:当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用不着借贷,反而专门设立借贷的法令,这不是贻笑天下吗?!话虽有尖刻,却触着了“青苗法”的要害。
传统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小农经济是王朝政权的主要统治基础,它的盛衰是王朝政权强弱的温度计;然而,政府苛重的赋税却又经常促使小农经济破产,重复地犯着自挖墙脚的错误。
因此,扶助小农经济的最好办法便是减轻国家的赋税。藏富于民,才能民富国强。王安石变法却根本没有改善农村生产关系和减轻国家赋税的任何想法,仅仅用借贷的办法以救燃眉之急,无疑是杯水车薪,起不了治本的作用。
二 名不符实
“青苗法”名为“济贫乏”,“实是放债取利”,意在给国库增加一笔财富。
“青苗钱”的利率实际并不低,年息是百分之四十,再加之由于粮食价格浮动而造成折换上的损失,进城请领的花费,向衙门胥役贿赂等项支出,当时人就认为其利率也有“一倍之重”,与私人高利贷相差无几。
这样,贫弱的小农每年一到稻谷登场,交纳“两税”之后就已经是“簸糠麸而食稗秕”了,怎么能保证交纳得清“青苗钱”呢?遇上连年灾荒,那更是一筹莫展。这就生动说明了,如不改善生产关系,想从小农身上多收一点以丰富国库的想法也会落空。这也就是“青苗法”最终无法坚持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时人(谷霁光等)已经有专文指出,作为改革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有不少闪光的成分。但是,我认为必须补充说,他的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导致了新法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
王安石具有进步倾向的经济见解绝大多数都产生在四十一岁之前。他四十余年生活在基层,历任地方官员廿余载,深知国情,久谙民俗,对官僚主义的恶习和弊端有切肤之痛。他认为积累、消费要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他原先也不太赞赏赈济之类的“救民”措施,说:“某窃谓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富才能国富,“富民”之道才是根本。他十分强调“理财”,“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度世之宜”,则不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
这表明他对经济的客观法则是尊重的,至少主观上不想悖其道而行之。更难能可贵的是,从地方从政实践中,他意识到官僚主义的行政干预有碍国计民生,曾主张改革茶、盐专卖,由商人自由销售,政府收税,主张在流通领域减少或削弱行政干预。他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对待人的物质欲望的态度,都较同时代人要开明得多。
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无愧于改革家的称号,在中国古代史上享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们从总体的角度考察新法,就像有些史学家(王曾瑜等)所揭指的,不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相反倒是仍在继续强化这种干预。地位的变化,从政方向的变化,使王安石当政主持改革大局后,实施方针与他原有的经济思想发生极大的偏差。自然也有怪不得他的地方。
在他上面有神宗皇帝,他只关心国库由瘦变肥,好让在深宫之中的他高枕无忧。有材料说明,王安石与神宗之间从思想到举措方面不无分歧,前者必须听从后者的“圣意”,否则只能以辞官了事(从二度辞官,即可了然)。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肯定王安石变法者常常提到“抑兼并”。
其实对“抑兼并”也必须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到北宋,城市与农村的私有经济发展出现新的机遇,建立在农业发展之上的城乡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活跃。用行政的手段,靠国家强势控制商品流通的办法,以及近乎搜括的加税加赋,打击富民,抑制分化,其结果虽暂时地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从长远说却摧残了商品经济,抑制了新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生,不利于新经济成分的孕育,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因此到了明清之际,进步的思想家如王船山、黄宗羲等,明确提出了反“抑兼并”的主张,这就说明了历史的必然性。
王安石晚年倾向消极。
他无法理解变法失败的社会原因。他在《偶成》一诗中感叹:
“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
“高论颇随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看来,他是把失败原因归咎于社会风气与人心的败坏,连诉说苦涩的老朋友也找不到了。
因而,他不能不深感孤寂悲苦,迷惘莫解。我不知道半山青灯读佛书,是不是曾多少缓解过他内心的苦悲?然而,他至死也不可能悟解:他所感叹的“吏不良”,并不纯粹是个人品质、道德修养问题,也不是靠个人的人格力量所能力挽狂澜的。从根本上说,一切都早由传统的专制主义官僚体制先天命定了的。此时,我们还不如模仿小说《极地之侧》,替王安石解脱,毕竟是:“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转载或引用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部分源自互联网,无法核实真实出处,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