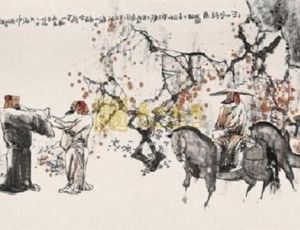子夏:身体力行的儒学教育家
卜商,字子夏,南阳温邑人,因擅长《诗》、《书》、《礼》、《乐》,文学造诣深厚,而得到孔子的青睐。他是孔门十哲之一,又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门十哲都是孔子学生中最优秀的人,包括大家熟悉的颜回、子贡、冉有、子路等等。他们品格高尚,各有所长。其中,颜回以德行居于首位,而子夏则以长于文学居于十哲之末。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学最重德行。所以“三月不违仁”的颜回,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那么,对于文学见长的子夏,孔子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师是指子张,其为人清流不媚俗,非常重视德行修养。他曾经把孔子说的“言忠信、行笃敬”恭敬地记在衣带上,以便随时提醒自己。因其修行方式有点与众不同,所以孔子认为子张的修行没有掌握好“度”,是偏离了中庸之道的,便是过犹不及。
而子夏则相反,孔子认为他在悟道和修行上还欠火候,即是不及。虽是回答子贡的提问,可能也有鞭策的意味,但依据孔子对学生的了解,一针见血,也许是因材施教的必要手段。到底是什么地方,让孔子觉得子夏德行不足呢?
君子儒就是要有大格局,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小人儒”限于个人层次,孔子提醒子夏不要成为没有大格局、只顾自己修身养性的人。潜台词是,子夏有只顾埋头于眼前的修行的倾向,而欠高远的格局。
对于求道,孔子说的很少,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以这样理解:其一,明心见性,每个人对道的体悟是与修行功力息息相关的,所以不便说;其二,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果德行尚未达到一定高度,怎能异想天开,想要通达于道?所以不愿说。虽然道的高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子夏明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以借助学习渐渐接近君子儒的高度。
不过,孔子也曾毫不保留地对子夏的好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洁白的纸上画的画真美啊,这是为什么?”孔子回答:“先有白纸,才有美画。”
子夏由诗经的诗句便领悟到“复礼”其实有相同的道理,仁德之心才是复礼的基础。他举一反三,由诗发散到学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儒家把礼、义的思想与诗、乐完美结合的教育理念。因此,孔子很满意子夏的勤思。
这归功于子夏从孔子继承到的修行养德之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他研究文学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成了他以后能把儒家思想扩展、深耕的法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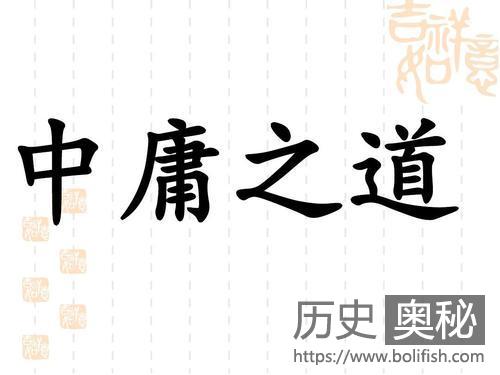 子夏:身体力行的儒学教育家
子夏:身体力行的儒学教育家
这是孔夫子对子夏的又一次“敲打”,因为子夏有功利心,急于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孔子担心他会偏离从政的根本之道,“居之无倦,行之为忠”,为官者心要始终公正无倦,才可能在政治上达道,而不会为蝇头小利所迷惑。
张居正评价道:“子之为政,必须志量广大,不可见些小利事功便以为得。何也?盖政以能通达为贵,然必须渐而后可以达也。若欲速,则求治太急而无次第,欲其通达,反不能达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若见小利,则其心已足而无远图。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见小利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以德行为重、无欲速、无见小利的儒家学者,想要在当时的官场上周旋,并有所建树,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孔子周游列国十几年,而无能用之者,可见一斑。或许当时的子夏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有意志动摇退而求小利的想法。
孔子过世后,子夏毅然决定放弃从政,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之所以踏上教育之路的原因,我能感同身受,与其为改变现有黑暗的官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专心把未来从政者的思想匡正,这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他转而投奔魏国,开始自己漫长的教授儒学的职业生涯,想不到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教育事业。那么,他对儒学教育是如何身体力行的呢?
那时正当魏文侯执政,这位有名的礼贤下士的一代名君,拜子夏为师,并任用了李悝、翟璜为相,内修外治,使魏国成为中原霸主。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是子夏的主张,“信”为立身、立国之本,作为统治者,必先取得百姓的信任,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为其所用。作为官员,也是同样,必先取得统治者的信任,才能上通下达,陈述的意见才能被接受,而不会被误解为诽谤。这些理念对魏文侯治天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时魏文侯与大臣之间互相信任,政治生态环境很自由,从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窥之一二:
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我何如主?”群臣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资治通鉴·周纪》
由上述可见,任座毫不避讳,仗义执言,文侯却以为上客,君上最终听从了臣子翟璜的建议,可见彼此互相信任。能有这样的臣子,是文侯的幸运,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君王有仁德之心所致。所以,像魏文侯这样的国君能得民心是可以想见的。
子夏在魏国,除了尽力做魏文侯的老师,还收受了三百多个学生,将自己一生所研究的诗、书、礼、乐的所思所感,尽心传授,并积极推行儒家的治国方法,创立了“西河”学派。在西河区域,人们甚至只知子夏,不知有孔子,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居于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嫠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汉代的徐防说:“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孔子带领弟子们修订了诗、书、礼、乐,使儒家思想明确了框架和范围,而子夏则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度挖掘,不仅令后代学者更易消化,而且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子夏是深得孔子真传的弟子之一。子夏不仅熟读儒学经典,而且像孔子一样仕途不顺后,选择了教育、讲学。他的学生中不乏杰出人才,李悝是战国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吴起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影响力就随着学生们的传承,不断放大,这一点是不是也很像孔子?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转载或引用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部分源自互联网,无法核实真实出处,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